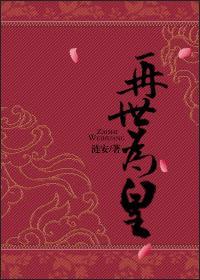梧颜提示您:看后求收藏(书神小说网www.hengjiefastener.com),接着再看更方便。
按照s城丧礼的惯例,遗体在家陈放两晚后,翌日中午就会前往殡仪馆火化。
昨晚,我,四哥还有几位表哥都在灵堂守灯,午夜过后,大家吃了点夜宵继续值夜,到了两点过后,陈安妮扶着寥玉珍也来了,寥玉珍憔悴无神得像个木头,我看见她默默垂泪了一晚,翌日一大早,陈安妮劝她吃饭,她倒是吃了,可是吃着吃着就抱着碗大哭起来——
我以为我很了解这个女人,她精明,说话刻薄毒舌,最擅长“攻击挖苦”我,但她也处处维护她的家庭,极力保护着她的女儿和丈夫。她珍视她所爱,这是爱人,而不一定要爱我。一如我,无法摒除一切去爱她。
偌大的一个灵堂,我突然觉得她才是那个最可怜的人。
我怔怔地出神,麻木地给前来吊唁的客人答礼,本来灵堂前的蒲团上跪着哭丧人——她三十多岁,身材微胖,痛哭流涕了三个时辰,还不时捶胸顿足,哭喊嚎啕,嘴里念念有词似在念什么咒语,一头蓬乱的头发随着她一起一伏前后飘飞,哭得哀泣,令人动容。
在大家惊讶的注视下,寥玉珍突然走上前将那个雇来的哭丧人一下推倒在地,然后自己扑通一下跪倒在蒲团上,对陈安妮说:“谁让她进来的?赶紧让她走!”
哀泣的乐声猝然停止,片刻,又继续。
那女人错愕地望着她,脸上的泪犹自往下淌,似乎受了莫大的委屈,双手往地上一趴即刻又要开哭,陈安妮见寥玉珍神色激动,虽也是一脸迷茫但还是赶紧上前将那女人扶起来,女人上半身直起来,膝盖还跪在地上,陈安妮在她耳边说了句什么,她即刻一擦眼睛起身跟着陈安妮走了出去,眉梢都染了喜色。
我认识这个女人,在我还在上高中的时候,家里请的保姆就是她,不过后来被寥玉珍辞退了,说是她手脚不干净,因为当时她哭天抢地喊冤枉,所以我对她的印象很深……没想到,这么多年过去,竟然在这里遇到,还是以哭丧人的身份。
虽然我从小在s城长大,但是雇佣哭丧人这样的习俗我从来未接受过,既是哭丧,如若不是亲人哭送还有什么意义?
现在正好,寥玉珍可以自己哭一哭了。
灵堂内哀乐大奏,哭声不绝,很快,亲友们便相继进到灵堂内开始“送别”,其实就是大家点香围着冰馆走一圈聊表哀思,我和陈安妮走在最前面,苏幕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,我偶尔一瞥眼就能看见他,不知道走了多少圈才被叫停,然后大家都把香扔到一个火盆里。
接下来是午饭时间,人一下子走散了,我搬了凳子坐在冰馆边,屋子里静静的,只有我和爸爸。
我坐了好一会儿,不知道脑海里浮现的那些画面是真实还是虚幻——当我执拗地等待他们来接独孤湘湘的时候,我个人住在偌大的一栋楼里,是一个叫陈明义的叔叔带我回家并且给了我一个新的名字。
那以后,才有后来的种种。
“冰冰,先去吃饭。”二嫂过来喊我。
出了灵堂,进到花园里临时搭建的木屋,我跟二嫂去饭桌旁坐下,一桌都是我熟悉的人,苏幕还未动筷子,隔着一张圆桌,他朝我递过来一眼,眼神柔软得像一摊雪水,很容易让此刻的我彻底卸下防备。我低垂着头没回应他,直接在二哥身边坐下来。
二哥和二嫂时不时给我夹菜,“这道笋做得不错,你尝尝。”二嫂将笋干夹到小碟子里给我,我夹起来放到嘴里慢慢咀嚼,然后吃了一口饭,这时,苏幕也站起来给我夹菜,我抬头看了他一眼,他夹了我最爱吃的土豆,果然,短暂的几天,他已经知道了我的喜好。
二嫂笑道:“倒是我没考虑周到,大哥该坐在这里。”她说完,理也未理我这个当事人的意愿,径自过去和苏幕换了座位。
大家都知道苏幕就像我的亲哥哥一样,自然会认为我现在很需要他。
事出突然,苏幕的事我还没有跟大家提,不过,他也确实很善于观察,不需要我在旁指导,完全能适应这个角色。
可事实就是,苏幕一坐到我的身边,所有盯着我担心我给我夹菜逗我开心的人全都自顾自埋头吃饭去了,显然,他们认为我有了苏幕其他一切都好说……
他会挑掉豆芽里的韭菜,然后只夹给我豆芽,会挑带筋骨的肉给我,因为全精肉我从不吃,知道我喜欢吃胡萝卜和西兰花……
他做得非常自然,就像他做惯了的,而且记得分毫不差。
我望着碟子里红红绿绿的菜,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,干脆埋头吃饭。
三嫂笑着搡了搡三哥的肩膀,“多跟大哥学学,老婆就像妹妹一样要贴心照顾的,知道不?”三哥忙笑着赔礼道歉,一边去给三嫂夹菜,沉闷的气氛才缓解些。
陈安妮和舅舅坐在一桌,我无意间抬头却看见她在打量我和苏幕,我垂下眼睛埋头吃饭,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。
饭毕,姑妈将我身上的衣服理了理,又在白布上给我夹了什么东西,然后叮嘱我一番,我粗粗记下,姑妈见我一本正经要去打仗的样子,安抚我:“别紧张,待会司仪会告诉你怎么做的,别出错就行。”我点了点头和她一起进去。
在户口簿上,我是长女,这些事自然该我来做。
我也要做,送爸爸最后一程。
鼓乐起,喧天。
客人都站在灵堂外,站了好几排,乍一眼看过去,一片黑色的影子。
我走进灵堂,冰棺马上要打开,已经有两个男人拿了工具站在两侧。
姑妈握了握我的手臂,我朝她点点头示意她放心,低声说:“那是爸爸,我不害怕。”
她欣慰地看着我,“去吧,送你爸爸最后一程。”
我颔首,从容肃穆地朝着冰棺走过去,末了,在冰棺右侧站定。
“开棺吧。”
随着一道清晰低沉的声音响起,两个男人开始动作,廖玉珍也牢牢地盯着冰棺,并且把陈安妮拉到身边,“看清楚了,记住你爸爸的样子。”
陈安妮一滴眼泪就掉了下来,她抬手拭去,目光紧紧地盯着慢慢开启的冰棺,嘴唇抿紧。
冰棺里逸出刺骨的寒气,还有檀香的味道。
他穿着中山装,身上盖着一张偌大的挽联,纸上有道家的八卦图案,冰棺里还放着很多锡箔纸做的“大元宝”,看上去花纹繁杂,手艺甚巧。
我按照叮嘱揭开他脸上的红布,指尖不经意碰到他的脸颊,一凉。
皮肤似雪,他闭着眼睛,很安详。
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怖。
“爸……”陈安妮已经抱着廖玉珍的肩膀哭了出来,然而,奇怪的是,我非常平静,眼眶出奇的冷。
我接过姑妈递过来的饭碗,拿过筷子,开始给在场的亲属喂米饭,走到苏幕跟前,我平静从容地夹了几粒米抬起来送到他嘴边,他看了我一眼,低头吃进去。
最后,我自己吃了一口,然后喂给爸爸。
“好了。”司仪叫停,然后让我去外面。
我走到门外,乐声又突然响起来,我抬起碗猛地朝地上摔去,“啪”的一声脆响,碗瞬间四分五裂,然后我又将筷子折断。
大家都看着我,或许是担心,可现在,我真的还好。
少顷,里面的人都走出来站到门口。
然后等了一会儿,他们抬着木制的棺材出来了,棺材一出灵堂,随后便有人迅速地拿起扫帚将屋子里的灰尘往外扫。
我正好站在门口,瞬间被呛得不行,苏幕将我往后拉了拉,我几乎是靠在他身上。
从陵园回来,已经是下午五点,我们送走了亲友后,就去花厅商量后续事宜,大家都已经疲累到极点,纷纷躺在沙发上休息。
我和苏幕是最后到的。
廖玉珍正在说关于公司股份的事,语气听起来很激动,“安妮是他唯一的女儿,他怎么可能没个交代呢?”
我进去,廖玉珍倏地将目光投到我身上,冷冷地住了口。
律师也已经到了,他显然认识我,扶了扶眼镜说:“既然人都到了,我传达一下陈先生的遗嘱。”
大家围桌坐下来,律师摊开两份法律文件,一份是股份继承书,另一份我只看到几个字,不知道是什么。姑父又将爷爷留给我的股份让渡说明拿了上来。
廖玉珍望着这几份文件,神色凝重。
无疑,这些东西摆在眼前,不用说明也很明白了。
大家都冷静地听律师走了一遍程序,他总结道:“所以,之后陈之冰女士会成为天承物流公司的最高股份持有者。”他看向我礼貌地点了点头。
这些文件压倒性地为我而准备,我讶异,震惊,混乱……为什么都留给我?我对公司经营这方面是完全一窍不通,若说给我一小部分股安顿我的生活,这我还能理解,但是现在把公司给我实在令人费解。
不止是我,姑父和姑妈都露出困惑的神色。
四哥肃静地坐在我斜对面,只有他面容镇静,像是早就知道结果一样。
我蓦地想到廖玉珍之前说过的话,我一抬眼,果真,廖玉珍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一眼,然后继续听律师说:“但是陈先生在这上面附加了一个条件。”他说着将那一份文件交给我。
“股份让渡书有法律效应的前提是,陈之冰女士必须和陈培源先生缔结婚姻协议,并且委任陈培源先生为执行总经理。”
这话一出,大家都是一震。
我没敢去看苏幕的脸色,我站起身,“如果我不跟陈培源结婚呢——”陈培源是爸爸给四哥取的名字。
律师雪亮的眼睛从镜片后看着我,然后从容地宣读,“那么所有的股份都会转到陈安妮女士名下。”
廖玉珍的眼睛闪了一下。
我攥紧了拳头,这根本不是一个选择题,结果爸爸已经填好了。
我想了想冷静地问:“她需要和陈培源履行婚约协议吗?”
我这话一出,陈安妮沉寂的眼睛蓦地转向我,似乎透着几分不解,我没有理会她,只是再问律师。
他回答:“不需要。”
“好,那我知道了。”